12月20日,西非葡语小国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发表声明,称该国政府“如今认识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中国人民代表”,这一决定当即受到中国外交部“这是回归正确道路”的称许。仅一周后,12月26日,中国外长王毅和来访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外长乌尔比诺.博特略(UrbinoBotelho)签署了建交公报,恢复了自1997年7月11日起中断达19年半的双边外交关系。
收到这样一份“圣诞礼物”自然是台湾当局所不能堪的(据台湾方面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前不久还和台交涉过“大使”更迭和双边协议修订等事宜,让台方觉得“问题不大”),连日来“大陆搞‘金钱外交’台湾恕不奉陪”、“圣多美与普林西比胃口过大台湾觉得不划算所以放弃”,甚至“欢迎大陆给台湾‘减负’,这些包袱早就不想背”之类言语不断从岛上飞出,真可谓酸辣苦咸,四味俱全。
那么,“圣多美风暴”的“风烟”究竟是不是“金钱外交”?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外长博特略毫不讳言“金钱”和“外交”因素对该国作出上述抉择所起到的作用。他对英国路透社和法国《青年非洲》杂志都表示,该国在矿业投资、农业、港口建设、机场扩建等领域都“有投资潜力”,而相较于台湾,和大陆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显然更有利于这些“对我国国计民生有重大意义”项目的推进。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就非洲而言并非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这个国土面积刚过1000平方公里、总人口刚过20万的小国,国民经济主要依赖热带作物种植业,2015年出口总额不过区区900万美元,其中80%为干可可、巧克力、咖啡和胡椒(且在这些热带作物领域也并不具备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进口总额则高达1.275亿美元,主要是食品(30%)、燃料(21%),其它产品囿于购买力而微乎其微。经常项目下赤字高达1.185亿美元,是年出口总值的约12倍。在很大程度上,台湾对该国的援助起到填补年财政赤字窟窿的关键作用(2016年截止目前高达1500万美元以上,可填补该国1/8的经常项目下赤字缺口)。
那么大陆呢?大陆2013年起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设立了贸易代表处,截止2015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800万美元,而同年中国和非洲间的贸易总额高达1790亿美元,中-圣贸易可谓“连零头都不够”。
但正如和该国关系密切的西非大国喀麦隆《喀麦隆投资杂志》所指出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不想继续过这样靠经援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打算换一种活法”。曾经同样贫困的“半个岛国”——赤道几内亚,以及该国最重要的区域内贸易伙伴——安哥拉(进口食品的第一大来源国)通过发展港口业、渔需业和石油业,已成为西非发展速度最快的后起之秀,自认为在这些领域同样拥有很大潜力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看在眼里,自不能不羡在心里。尽管这两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关键——石油开采,投资“大头”并非中国,但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石——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却惟有中国愿意持续投入,且不论哪个国家资本所开采出的石油,最大买家也依旧是中国。既然邻国已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了现成的经济发展模板,这个岛国亦步亦趋地照办,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某些欧洲媒体所盛传的“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香港中基公司承诺贷款3000万美元换取该国改变外交立场”,则恐怕不足为训:这个“香港中基”(CIFL)并非什么“中国官方背景机构”,而是一间在香港注册的民间商业公司,且注册资金极少。这家公司曾在安哥拉搞出以“杭萧钢构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问题项目”,在加蓬、赤道几内亚也有类似“前科”,其所有人徐京华(SAMO HUI)曾经的亲密合作伙伴——以过去十多年来世界各地各种奇怪“运河项目”为卖点之商人王某,旗下公司某威也正面对一系列麻烦,即便真承诺了些什么,恐怕也很难成为“正能量”。
喀麦隆和安哥拉方面的经济界人士指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近年来积极谋求加入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CEEAC)的“区域一体化”(FTA)计划,就在“一中声明”发表的几乎同时,以该国金融部长多斯拉莫斯(Américod’Oliveira dos Ramos)和国民议会主席迪奥戈(José da Graça Diogo)还到访了中部非洲国家银行总部所在地——喀麦隆雅温得,并发表了“全心全意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声明。由于CEEAC11国经济缺乏互补性,这个组织早已将“和洲外大经济体接轨”当作区域一体化成败的关键,而“接轨”的重点,则是与既是最重要出口市场、又是最重要进口产品和投资来源的中国,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接轨”。“在这种情况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出于金钱和外交两方面的考量,作出怎样的抉择不言而喻”。很显然,该国所谋者大,且这些“所谋”,今天的台湾即便想给,也是无论如何给不了的。
然而,“金钱”和“外交”的考量并不是什么“金钱外交”的考量。非洲历史上的确出现过“金钱外交”的一幕,却并不是现在。
在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曾向非洲提供了数额巨大的无偿援助,这固然收获了丰硕的外交回报,在经济上却是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所不能堪的,且吊高了部分非洲国家的胃口。1982年12月起,时任中国总理出访非洲11国,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新的四项原则,开始在对非援助方面“量力而行”,1995年下半年,又对援外方式作了重大改革,变原先的无偿援助为主为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对这种改变,一些非洲国家不理解、难接受,认为中国不再慷慨,甚至说“中国得到的西方援助越来越多,给非洲的钱却越来越少”,这种变化加之冷战后西方对非洲的重新重视和投入,以及台湾的金元外交,一度给中国在非影响力造成相当压力。1994年2月2-4日,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和台湾“建交”,与中国断交;1995年7月13-25日,西非国家冈比亚和台湾“复交”,和中国断交;1996年1月3-9日,西非重要国家塞内加尔步其后尘(当时笔者作为中国某民营大型公司国际经营部部长助理,正和塞内加尔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处洽谈投资合作业务,所受到的冲击和震撼,至今记忆犹新)……96年台海危机爆发,中国重新在非洲“主动出击”,已崭露头角的中非经贸关系(在90年代中至本世纪初的约10年里,民间贸易占据关键地位)则成为探路先锋,1998年1月1日中国和此前并无外交关系纪录的南非建交,成为台海两岸“非洲外交交兵”攻守易势的转折,2005年10月25日,曾被称为“台湾在非洲‘金元外交’最大收获”的塞内加尔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复交;2007年12月28日,同样此前从未和中国建交的马拉维宣布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台湾“断交”,此后双方心照不宣进入“外交休兵”状态。今年民进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后,“外交休兵”的默契不复存在,早在2013年11月14日就和台湾“断交”的冈比亚于今年3月17日与中国复交。
不难看出,“金钱外交”是在特殊阶段出现的外交特殊现象,且呈现“台湾先攻、大陆后反攻”的局面,1996年的台海危机是双方攻守的转折点,而西非不折不扣是这场外交战的主战场。恰巧这一时期笔者的工作和西非国家有许多交集(后期曾常驻西非多国),对于海峡两岸在这场鏖战中的成败利钝乃至“关心则乱”(一位西非某国外交部官员曾私下对笔者坦言,他们中有人曾谎报“对岸有特使即将到访”向另一头索要“疏通费”,得手后再以“经我多方疏通对岸特使被拒之门外”报功,“什么都不做就能大赚一笔”),都有深刻体会。当时两岸先因自身利害权衡在非洲“收缩”,继而又因政治博弈因素不计成本“对进”,被一些具有周旋洲外势力间丰富经验的小国钻了空子。当时大陆在外交和国际政治领域尚不具备今天的实力,在经济领域更处于艰难转型期和被非洲各国认为“变吝啬了”的过渡期,和“四小龙”之一的台湾间并未拉开什么差距,“金钱”和“外交”都不具备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金钱外交”自然有缝隙可钻。
如今情况大不相同,大陆在“金钱”和“外交”两个层面都具备在非洲范围内对其它大经济体的相对优势,和在全球范围内对台湾的绝对优势,所谓“金钱”和“外交”,其实就是“经济考量”、“国际政治考量”,是任何国家作出外交抉择的最基本考量要素,在这两个要素上的绝对领先,就足以在需要的时间赢得需要的成果(前提是自己不犯错),而无需“金钱外交”这种“没办法的办法”来助阵。
大陆不再需要“金钱外交”作为补充手段,台湾却仍然需要:目前台湾保持“邦交关系”的21国中还有两个非洲国家,弹丸小国斯威士兰从未和中国建交,但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虽然自1994年起就和中国断交,但两国间经贸投资关系一直有所发展,布基纳法索瓦瓦加杜古第二大学2015年11月发表了《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对我国经济之积极影响》(l'expansion desrelations économiques et commerciales avec la Chine a un impact positif surl'économie du Burkina)专题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012年布基纳法索对华出口同比上升32%,自中国进口同比上升34%,“和中国复交并发展经贸关系正当其时”。尽管直到11月,布基纳法索总统卡波雷(Marc Roch Christian Kaboré)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为台湾说话,但这被非洲许多观察家认为和去年12月16日该国对台湾“喊价”得手、获得20个合作(台湾投资)项目息息相关,而近期该国也不断明里暗里催促“兑现新承诺”(指去年12月16日会议后短短几个月间布方报出的一系列“大手笔”要价项目)——正如许多当地工商界、政界人士所言,除了硬着头皮“跟进”,台湾恐别无选择,毕竟在仅剩的21个“邦交国”中,布基纳法索是面积最大的一个,面积“高达”27.38万平方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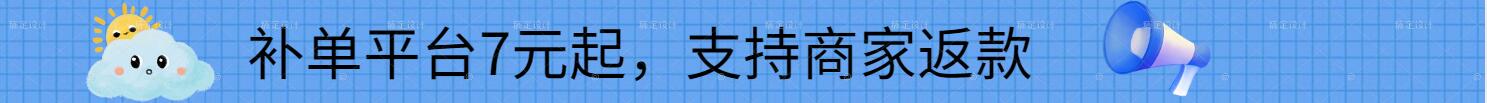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