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尔迪齐《纪闻花絮》第十七章
一、突厥的起源和特征
(一)雅弗的传说
乌贝达拉赫·本·胡尔达德贝赫(*’Obeido ‘llah Ebn-e-Xordāδ-Beh,有时写作lbn Xurdāδ-Bih)在他撰写的《记述之书(the Book of the Reports)》中说,突厥人属于中国人的后裔。[然而],阿布·阿穆尔·阿布达拉赫·本·穆卡法厄(Abū- ‘Abdo-’llahWbno-’l Moqaffa’)在他的著作《世界的四分之一(The Quarter of the World)》中说,当预言者诺亚(Noah)走出方舟的时候,世人已经绝迹。诺亚有三个儿子:西姆(Shem)、哈姆(Ham)和雅弗(Japheth);他把世界分给了他们三个。他把黑人——阿扎尼亚人(Azania/Zanj)、埃塞俄比亚人(Abyssinia)、努比亚人(Nubia)和柏柏尔人(Barbary)和巴匝尼亚人(Phazania)[0]的土地,以及波斯沿海与[南部]地区——给了哈姆;而伊拉克(Iraq)、呼罗珊(Xorāsān)、汉志(Hejāz)、也门(Yemen)、叙利亚(Syria)和伊朗的领土(Irān-?ahr)成了西姆的财产;突厥人、斯拉夫人的土地、高格(Gog)与玛高格(Magog)部落,[①]直到中国之地归雅弗。因为突厥斯坦地区远离人烟稠密之地,故被称为Tark(阿拉伯语,意为被抛弃或受到忽略之地)。[因此],诺亚心怀平静,向至高无上的神进行了祷告,请求教给雅弗一个名字,使他一说出这个名字,[立刻]就下雨。神马上听见了他的祷告并教会了雅弗。
(二) 突厥人是如何开始使用诈答石的
雅弗既知此名,便将其写于石头上且小心翼翼系之于项,以免遗忘。每当念起那个名字求雨时,雨就应声而下,如果把那个石头放进水里再把水给病人喝,病就会痊愈。作为遗产,该石头一代代传给后裔。后来人口繁衍增多,形成了虎思(?uzz)、葛逻禄(Xallux)、可萨(Xazar)和其他一些人群,于是,因为石头而发生了争执。
[先时],石头在虎思人手中,大家决定找个日子聚集起来抽签,谁抽中了石头就归谁。[然而],虎思人拿了一块形状与之一样的石头并在上面写下那句祷词。其首领把假石头挂于己项。到预定之日抽签,签被葛逻禄抽上了。那块假石头给了葛逻禄人,而真石头仍然在虎思人手中。突厥人借助于石头求雨的习俗就是这样来的。
[突厥人的特征是有]稀少的胡须和犬一样的性格,那是因为[雅弗]在孩提时病了一场,什么药也不起效。最后,有个智慧老孺告诉雅弗母亲,给他吃蚂蚁卵和狼奶,或许能够治好其病。此后,其母用这两样东西喂了他一个月,才将其治愈。[然而],当他开始长起胡须时,胡须却疏疏落落,其后裔也长成了这样。总之,稀疏的胡须来自蚂蚁卵,而凶狠的性格来自狼奶。突厥人就是他的后裔,现在,我将像我在各种书籍中看到的那样对他们逐一给予描述。
二、葛逻禄[②]
(一)叶护葛逻禄起初何以成为九姓乌古斯的奴仆:叶护的传说
谈到葛逻禄,人们说葛逻禄是突厥诸首领中的一个。[那个时代],突厥人从一处向另一处迁徒。[一天],葛逻禄之母在空旷无人处骑马,葛逻禄的一个仆人走近葛逻禄的母亲,想占有她。于是他把她抓住并搂住她,那个女人轰走了他,并进行了威吓——如所周知,突厥妇女俗尚纯洁——仆人见状生畏而逃,投于可汗统治下的九姓乌古斯人之地。可汗的一个[下人]在狩猎时于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发现了他,见其将毛毡折起来披在身上。这个下人名为叶护,前来觐见可汗。可汗知晓其情后,命令当地所有的葛逻禄的人召集起来,当即任命该叶护为其首领,并把该部命名为叶护葛逻禄。[③]
(二)最高权位如何经由[西]突厥而传给葛逻禄
此后,有一个人从[西]突厥斯坦(即七河流域)来到了九姓乌古斯部落,爱上了叶护的一个未婚女子,把她盗走并弄到[西]突厥斯坦之地。[然而],[西]突厥斯坦汗又从他手中夺走了那个处女,让她和自己生活在一起。可汗待她很好,给她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告知她的情况,并邀请他们到自己这儿来。家人到后,他慷慨以对,并邀请该部其余的人(即所有的叶护葛逻禄部落)都过来。当这个消息传过去后,部落所有成员都到了那里(即西突厥斯坦)。当他们聚集多了,可汗便让在自己领地内居住下来,按照习惯,给那些缺衣少食,无所依靠者分配了土地。
他们所有人就以这种方式生活着,直至突骑施人向可汗的人民与[氏族]、[部落]发起攻击。他们杀死了民众中享有盛名的十二个首领,挥剑砍杀所有可汗臣民。兹后,可汗大帝国落到了葛逻禄[首领]Chong Chüen(?ūn?ān)之手。可汗家族中最后一个被杀死的是胡突格兰(Xoto?lān)可汗。第一个登上王位的葛逻禄人是伊勒玛勒玛逊(?l-Malmasin)叶护。政权落到了葛逻禄人手中。突厥斯坦的许多部落都起源于这个叶护葛逻禄部落,但关于他们的一些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三、寄蔑人[④]
(一) 它们原来何以成为鞑靼的一支:设的传说和也儿的石名称的由来
至于寄蔑人,其起源是这样的:首领鞑靼死后留下两个儿子,长子治国,幼子对哥哥产生了嫉妒,幼子名叫设(?ad)。他试图弑兄,但未得逞,遂心怀恐惧。
那时,设爱上了一个女孩,携之逃离其兄,投奔一处毗邻大河之地,那里林木葱茏,有大量飞禽走兽。他在那儿扎起帐篷,安置下来。此人每天和女孩双双外出狩猎,吃猎物肉并用黑貂、灰鼠和银鼠皮做衣穿。
以后,又有七个鞑靼(Tatār)亲戚来到他们这儿。第一个是乙密(?mī),第二个是咽麺(?mäk),第三个是鞑靼(Tatār),第四个是巴彦德尔(*Bayādur),第五个是钦察(Qif?aq),第六个是拉尼卡兹(Lānīqāz),第七个是阿吉拉德(Ajlād)。这些人牧放着主人们的畜群,但缺乏牧马之地,在寻找牧场时,他们来到了设所在的地方。那个女孩看见他们后便跑出去喊道:“额尔齐斯(erti?)”,意为“站住”。正是因为这个缘由,这条河便被命名为额尔齐斯(erti?/Irtysh)了。
大家认出了那个女孩,都停了下来,撑开帐篷。设回来时带来大量的猎获物,招待这些人,[于是],他们都留在那里直到冬天来临。下雪了,他们回不去了。那里水草丰美,[于是]他们就在那里过了一冬。
当积雪融化,万物复苏之时,他们支使一个人回到了鞑靼人的营地,想让他带点儿那个部落的消息。但那人到后才发现,该地已变成一片废墟,人烟断绝。原来是敌人来了,抢掠和屠杀了全体人民。部民孑遗从山脚下朝他奔来。他向他们讲述了设和同伴们的情况,大家遂朝着额尔齐斯河进发。到那儿之后,他们向设致敬,并拥立设为自己的首领。另外一些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开始前来,竟聚集起了七百人,在设的统领下,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嗣后,他们得到繁衍,沿山而居,并形成了七个部落,分别以前面提到的那七个人的名字作为部落之名。
(二)寄蔑人何以崇拜也儿的石河,以及都督称号的由来
所有这些寄蔑人的特点都是脾气暴躁、吝啬、不好客。某一天,设及其子民站立于额尔齐斯河畔,听到一喊叫声传来:“喂!设!我在水中,你把手伸给我!”但除了水面飘浮的头发外,设什么也没看见。他拴住马,走到水中抓住那头发,原来那是他的妻子可敦(Xātūn)。他问她:“你怎么掉下去了?”夫人回答说:“鳄鱼(nehāng)把我从河岸上拖下来了。”[自那之后],寄蔑人敬仰这条河,崇拜这条河,拜倒于河边,称这条河是寄蔑人的上帝。对于设,他们赠送其“Tutuq(都督)”的称号,[⑤]意思是:他听到了声音,迮进水中却毫无畏惧。
(三)通往寄蔑国之路
至于通往寄蔑[国]的道路,那是从法拉布(Pārāb,即讹答剌)出发往新城(Deh-e Nō,即Navē-kaθ/Yabgī-Kent)[⑥]去,在新城通往寄篾[国]的路上有一条河,渡过该河就进入一片沙漠荒地,突厥人称之为?tūqman或?lūman。再往前到达索库克河(Soqūq),过河是一片盐沼地(sūrestān),再向前往肯迪尔塔格山(Kändävūr Tä?i)走。此山过后是一条河。沿河而行,绿荫、青草和树林掩映,直达河源,那里山峰高耸,有一条狭窄的山间小路可通山顶。越肯迪尔塔格山再向阿索斯河(Asos)前进,可通往寄篾[国]。这段路需要五天行程,由于树荫蔽天,太阳光照不到人身上,直达被称作阿索斯的大河。河水呈黑色,从东方滚滚而来,流到塔巴里斯坦(Tabarestān)的入海口。由阿索斯河前行,即达额尔齐斯河,那是寄蔑[国]的第一个前哨基地。
(四)寄蔑国的几点独特之处
沿河四周有许多野马,随处可见一两千匹,系国王坐骑变野后不断繁殖而来的。要抓住这些马除套马索别无他法,抓住之后,骑上进行驯服,一旦驯服,就和人混熟了。
额尔齐斯河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站在河边,对岸的人由于距离太远而认不出他来。河水是黑色的。
渡过额尔齐斯河就来到了寄蔑人的帐篷前。他们没有低矮的建筑物,大家住在树林里、峡谷中和草原上.拥有大群牛羊,但没有骆驼。如果有商人牵一头骆驼途次该地,那牠在这儿也活不了,因为骆驼一吃这里的草就马上倒毙。当地不产盐,自然地,如有人带来一曼(mann,即Patman巴特曼,容量单位——译者)盐,他就会得到一张银鼠皮。他们的食物在夏天为马奶,称作Qumïz(马奶酒)。冬天,他们吃储备好的羊肉干、马肉干或牛肉干,各储多少要看自己的财产情况而定。这个地区雪大,草原积雪有时达一长矛之厚。冬天,他们带着牲口前往伊格拉克(??raq)省,[⑦]到达玉克·塔格(Ükü-Tä?/Kök Tä??)。他们有用木头建造的地下水池,以备冬用。雪下得过大时,他们便饮用在初夏时节储存之水。牲口不能外出饮水,就喝雪水。寄蔑人狩猎的对象是黑貂和银鼠,他们称其首领为依难叶护(yīnāl-yab?ū/īnāl-bay?ū)。
四、样磨[⑧]:部落如何形成
提起样磨部来,[西]突厥可汗看到葛逻禄人数量多了,力量强了,就同吐火罗斯坦的嚈哒人(Hephthalites~Habtālān)交往起来。那些人向他们要女人,葛逻禄人就给他们女人。同时,可汗发现[西]突厥斯坦的衰弱并有些担心自己的统治。此后,九姓乌古斯的一部分离开自己的部落外逃,投于葛逻禄人,但后者无论如何不能同他们和睦相处。[西]突厥可汗叫他们迁居在葛逻禄人和寄蔑人的领地之间,他们有一个首领,名叫菩萨帕瓦达(Bodisatv-Pavard)[⑨]。他们之间发生了内讧,一部分逃往突厥可汗的附近。当他们来投样磨后,发现与他们相处甚好。样磨人很富有,有很多牲畜和优美的中国紫貂皮,都被运往外地。其地距离中国西北部需要一个月的行程。他们向突厥可汗派去使者,向他报告他们的处境,说道:“我们来为你效劳,如果你允许,不管居于何处的样磨人都可出击。”突厥可汗甚喜,款待了他们并答应其请求。葛逻禄人袭击了他们。他们在蒙受重大损失后离开那里去投寄蔑人。未久,设都督开始欺负他们,要其交纳贡赋,使之再受伤害。于是,他们寻求突厥可汗的佑护,离开葛逻禄和寄蔑之间的地方而入居可汗领地。可汗仿照设都督的称号而给样磨首领以样磨都督的称号。
五、黠戛斯[⑩]
(一)部落如何形成,他们与斯拉夫人的联系,他们何以皮肤红润,失名斯拉夫领袖的传说
黠戛斯人团结于领袖之下,原因如下。他出身子斯拉夫人,为Yigän (Yegän Yaqlar)[?]之一。从拜占庭(Byzantines/Rūm)来了一位使者,到达斯拉夫之国,有人杀死了那个使者。他被杀的原因在于拜占庭人起源于诺亚的儿子西姆,而斯拉夫人源于雅弗。他们的名字与“狗”这个词有关,因为他们是用狗奶喂大的。是这么回事:当人们为了雅弗而取蚂蚁卵时,蚂蚁就祷告了,希望至高无上的神别让雅弗得到儿子的孝顺。雅弗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阿什克纳齐(Ashkenaz),两眼都失明。那时,狗有四只眼睛。雅弗有一条狗,正好这时生仔了,雅弗杀死小狗,他的儿子遂在四岁以前一直吮狗奶,抓着狗的耳朵走路,如同盲人行路一般。那狗生了第二胎之后,就抛弃了雅弗的儿子,并感谢神使它摆脱了他。第二天发现,狗的两只眼睛转给了这个孩子,狗只剩下了两只眼睛。原先那两只眼睛的痕迹还留在狗的脸上。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被称作sag-lābī(Saqlābs,斯拉夫)人。[由于]那个首领在争执中杀死了使者,因而必须离开斯拉夫人的国家。
他离开那里后投向可萨人,可萨可汗至死一直善待之。然而,另一个可汗登极后从内心反感他。那人被迫远走他乡,投奔巴什基尔(Ba?jert/Ba?girt/)。
巴什基尔是可萨大人物人之一,居于可萨与寄蔑的领地之间,有两千骑士。此后,可萨汗派人到巴什基尔那里去,要他将那个斯拉夫人赶走。他将这个情况告知斯拉夫人,斯拉夫人遂投向九姓乌古斯的领地。他与那些人有亲戚关系。他沿路来到寄蔑和九姓乌古斯领地之间的一个地方。九姓乌古斯可汗同自己的部民发生了争执,很生气。部民被可汗杀死,孑遗四散,三三两两来投斯拉夫人。斯拉夫人接纳了他们并善待他们,因此他们聚拢了好多人。他派了一人到巴什基尔那里去,与他结盟,渐至强大。此后,斯拉夫人向虎思人发起了进攻,杀死了他们的好多人,抓了他们好多俘虏,聚敛了大量财富,有些是抢来的,有些是把全部俘虏卖为奴隶得来的。他把聚拢在他手下的那个部落命名为黠戛斯。当有关他的消息传到斯拉夫族人那里,他们就有许多人携带家眷财产来投奔他,同另一部分人联合起来并结成亲族,从而大家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斯拉夫血统的特征在黯戛斯人的外貌上还可以看出来,诸如红头发和白皮肤之类。
(二)通往黠戛斯国之路
至于从九姓乌古斯之地通向黠戛斯的道路,正是从中国城(?īnānj-kaθ)[?]往龟兹(Xusan)[?],从龟兹往NWXBK(或NWXYK),如同到达KMR’Z/KMZ’R一样远,需在草地走一两个月,另需在沙漠走五天。再从KMR’Z出发到达马纳巴格卢(Mānābag-lū?)需傍山走两天,然后走进树林,随后经过草原、[几处]泉水、猎场,抵达人称马纳巴格卢(Mānabag-lū?)的大山,山势巍峨,生有些许黑貂、灰鼠及麝羚,林木森森,猎物丰富,山里特别宜于居住。过了马纳巴格卢向曲漫山(Kökmän)[?]进发,沿途草原广布,清泉滢滢,且野味众多。在这种地方走四天就到了曲漫山。峰峦叠翠,道路崎岖。从曲漫山到黠戛斯地为七天路程,道路行经草原与牧场,路旁有众多清彻的泉水,树木翳日。因而敌人深入不到那里,条条道路像花园,直到黠戛斯本土。黠戛斯可汗的军帐就在这里,这是(其地)首要的和最好的地方。
有三条可行的道路通向[黠戛斯国]。[除上已详述的第一条道路外],第二条通道完全穿行于高山和丛林,与另一条道路纠缠在一起。三条道路中有一条通往九姓乌古斯,方向是朝南;第二条通往寄蔑和葛逻禄,方向是朝西走;第三条通向沙漠(bīyābān)。沿第二条道路走三个月可达被称为豁里(Qōrī,或作Fōrī、Fūrī)的大部落。这里也有两条路,一条穿过草原,需要三个月的路程;另一条往左走,需两个月的路程,但这条路很难走。整个行程中都必须沿着树林,在山间羊肠小路和狭窄的地方走,沿途到处积水,经常碰到河流,不时下雨。谁想走这条路,他就应当准备能放行李衣物的一个东西,路上无处不透水,地面上什么东西都没法放。要穿过这个遍布泥沼的地区,只有跟在马后面走。
(三)野蛮的豁里蒙古人[?]
在这些沼泽地里有野人住着,他们同谁也没有交往,他们不会说异族语言,而他们的语言谁也听不懂。他们是野蛮人,总是仰面朝天躺着,其全部财产都包在兽皮里了。如果把他们从这些沼泽地里领出来,他们马上就茫然无措了,就像鱼离开水一样。他们的弓是用木头做成的,衣服用兽皮做成,食物是猎获的动物肉。其宗教信仰在于任何时候都不碰别人的衣服和财产。如遇战事,便带着自己的家眷和财产投入战斗,战胜敌人后,并不动敌人财产,而是全都烧掉,除了武器和铁器外什么都不要。当他们有性接触的时候,要求女人四肢支撑,事后才与之婚配。聘礼为野生动物和树木。如果他们落入黠戛斯人之手,他将没有吃的,当见到自己的同伴时会逃避。如果他们之中某个人死亡,会把尸体抬进山里,悬于树下,直至腐烂与消失。麝香、毛皮和觳突角由黠戛斯地区外运。
(四)黠戛斯对尸体的处理何以有似印度教徒
黠戛斯人和印度教徒一样,把死者火化,并言称火是最纯洁的东西,一切东西掉进火里就变得洁净了,[因此]火将使死者脱离污秽和罪孽而洁净。黠戛斯人中,有些崇拜母牛,有些崇拜风,有些崇拜刺猥,有些崇拜鸦鹊,有些崇拜隼,还有另外一些崇拜高大而漂亮的树木。
(五)黠戛斯的预言家及其每年的预言
他们中间有人每年会在事先预定的某日过来,带来了全班乐师并筹办欢宴所需的一切。当乐师们演奏起来的时候,这个被称作佛吉暾(fo?itūn)[?]的人就昏迷过去了,然后大家就问他那年将发生的一切,即是否有灾难,丰歉情况如何,以及雨水和旱情、危险和安全、敌人的入侵。他们会一一道来,而且大部分都应验。
六、吐蕃[?]
(一) 从魔鬼崇拜者萨比特以降的世系
说到吐蕃人何以聚集成族,与一个名叫萨比特(θābit)的著名的希米亚提人(Himyarites)有关。这个萨比特受到也门国王——通常被称作托巴(Tobba)——的信赖。托巴授予萨比特国王中尉之职,萨比特从母亲那里得到一封短简,其中言道:“有一个托巴曾做过很多努力,向东方寻找一个国家,在那里植物是金的,土地是麝香,草是乳香,其他[植物]是芬香的,其猎物是麝香鹿,那里的山积雪覆盖,那里的平原是人间乐园。播种的土地饮用脏物与垃圾而非水。”当萨比特读到短简时,心向往之,聚集大军出征。当他到达西藏后,看到了所有的上述迹象,知道这里是宝地。他非常高兴。然而,正当高兴时,黑夜来临了,所有人相互都不认识了,魔鬼命其手下恶魔偷走了萨比特,运到空中。这时的萨比特身着胸甲,外边套上他人不曾有的礼服。恶魔把他置于高山之巅,他在那里一待就是二十天。随后,魔鬼化装为老妪,向萨比特走来,要萨比特朝拜他,成为他的从属与奴仆。萨比特言听计从。于是,魔鬼把萨比特带到山巅,放他下来,为其娶妻。魔鬼随后自己也下落,命萨比特与之成亲。萨比特照做,之后,魔鬼使萨比特头发高悬,恰像女人的头发。继后,他在他头上悬挂珊瑚(或玛瑙)念珠,并将一个长头巾绑在前额,然后从萨比特的侧身抓了一个虱子,扔进他嘴里而且吞下,说道:无论是谁,只要有欲求,生命就会延长,而且没有敌人,必须以动物为食。然后,他命萨比特杀死麾下由他点名的七个军将。兹后,萨比特要求他弥补缺额,并服从他的命令。魔鬼答道:他将变成可汗,整个国家将服从于他,他将变成所有部落之主。随后,魔鬼带萨比特从山巅坠地。他从军队中看到一个人在收集柴草,他看见此人正与化装为老妪的魔鬼一起朝他走来。萨比特向他询问部队情况。此人回答说,在他走后,他们之间发生了纠纷。此人问萨比特的情况。但魔鬼[代替萨比特]回答说,天使带他去见上帝了,已给他传下旨令,披上胸甲,送他归来。这个男人立即跑回营帐,把他听到的讲给士兵听。萨比特到达后,将魔鬼安排诸事一一落实,结果,他成了可汗。因为吃虱子、性开放、头发上悬如女人等原因,吐蕃可汗自认为是身穿用光明制成的护甲由天而降生的。
(二)通往吐蕃之路:塔里木盆地、于阗、可失哈儿、龟兹
说到去吐蕃的道路,要从于阗去Al?ān[?],而且是顺着于阗的丛山走。山中有人居住,他们拥有很多四条腿的牲畜,如公牛、公羊和牦牛。顺着这些山可到Al?ān。向前走是一座桥,从山的一边搭向另一边。据说,桥是于阗人在古时修建的。山从此桥一直绵延到吐蕃可汗的宫廷。那里有一座山,走进山中,由于空气稀薄,你会喘不过气来,因为没法呼吸,说话困难,许多人因此丧命,吐蕃人把这座山称作“毒山”。
如果从喀什噶尔走,那就要往右行,在两座山的中间朝东走,过了山就到了被称作Aδar的国度。该国绵延四十法尔萨赫(Parasangs),一半是丛山,一半是峡谷与平原。喀什噶尔附近有许多村庄和无数的乡邑,古时此国曾归吐蕃汗(Töböt Xān)所辖。从喀什噶尔地区往沙里木善克特(Sārimsāb-kaθ)去,再从那里去阿里苏尔(Alī?ūr)。沿着荒原走到库车河边,河流向库车(靠近莎车)。在河岸上的荒原边有一被称作Xamxāb(?amxāb/?amxān)的村落,有吐蕃人居住。那里有一条河,必须乘船而过,过了河就来到吐蕃人的边界。那里有一座庙,有许多偶像,就中一个坐于宝座之上,背后放有一个状似人头的木器之类,偶像则靠在这块形似人头的木头上。如果用手在偶像的背上摸一下,就会冒出火花来。此地左面是荒原,那里沿河有许多齐胸高的路旁树木。
七、巴尔浑[?]
(一)亚历山大时代它的波斯起源
说到巴尔浑的起源,出自波斯。原因是当亚历山大击败大流士(Darius),征服波斯,占有了波斯王国。波斯人聪明、足智多谋、勇敢,而且非常有知识、精明能干、善于观察,而且谨慎,这些都引起亚历山大的担忧。[所以],亚历山大推定他有一天他离开后他们将反叛,会杀害他的继承者。于是,他从每一大家族中抽出一至二人留在自己身边,作为人质。他出发到突厥斯坦,计划从那里征服中国。但当他到达今天被称作巴尔浑这个地方时,他的探子报告说,前面之路非常荒凉,仅有羊肠小道,缺乏饲料。所以,他随身携带的行李需要留在有饲料的地方。亚历山大发布命令,多余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要埋起来,牲畜要驮载饲料。他命令波斯贵族之子要在那里坚持下去,直到他从中国返回,然后他将带领他们返回故乡。服从其命令,他们都呆在那里,但传来的消息讲亚历山大在征服了中国后,又从那里去了印度,那些伊朗贵胄对返回故土感到绝望。于是他们派人到中国,带回一些工匠,如泥瓦匠、木匠、画匠,命他们在那里仿照波斯城市修建城镇,取名为巴尔浑(Barsxān),意为“波斯王子城”(Amīr Pārs)。
(二)通往巴尔浑之路
至于通往巴尔浑之路,从新城[?]出发,沿着通往炽俟之路,至于库姆巴尔卡特(Kūmbar-kat),再至吉尔(Jīl)。吉尔是一座山,意思是狭窄。[21]从那里达到雅儿(Yār)有十二法尔萨赫(Parasangs)远,雅儿是一个村庄,可容三千人。其中有炽俟特勤(Tegīn)的帐篷,但是没有固定的居民。路的左边(即北边)有一个湖,被称作热海(Issik-Kül/isi?-köl)。周长有七天的行程,有七十条溪流注入。水略咸。从那里至tūng地,有五法尔萨赫远,再从tūng地到达巴尔浑需三天行程。沿途除了炽俟帐篷一无所有。巴尔浑的Dehqān被称作mana?。巴尔浑之地可容纳六千人,热海周围有炽俟人定居。巴尔浑之南有两座山峰,一座叫叶护(Yab?ū/Bay?ū),另一座叫阿扎尔(Azār)。[22]有一条被称作Tafsxān的溪水从东侧流出,流向中国。第二座山峰很高,飞往中国的鸟都无法穿越。
八、九姓乌古斯[23]
(一)他们的起源:菊儿特勤的传说
九姓乌古斯是一个民族,其王被称作九姓乌古斯可汗。古时,九姓乌古斯可汗是一位人称菊儿特勤(Gür Tegīn=Köl Tegin)的人,其母为中国血统,其弟为可汗。菊儿特勤之母系自由民,来自阿跌(Az)氏。菊儿特勤之同父异母兄弟欲杀之,他割断其喉咙,将他弃于祖辈埋骨之地。菊儿特勤有一个老奶妈,把他送到摩尼教徒(Mānīyān)那里,并托付给选民(电那勿,Dīnāvarīyān)[24],期望他们用药治疗他,直到他恢复健康。后来菊儿特勤去了焉耆(Anki,Agin/Agni)城,[25]那是九姓乌古斯的都城,并躲藏起来。有几次他策划阴谋,消息传到了九姓乌古斯汗那里,可汗对之进行了抚慰。最后,九姓乌古斯汗在王宫召见了他。但是,九姓乌古斯汗不让他回到原来的部族,而是把北庭(Panj-kaθ,即Be?-Bali?)封给了他。后来,菊儿特勤渐起反叛之心。一方面善待领地里的人民,促进本族人口增长,一方面耐心等待时机。[最终],他得到了九姓乌古斯汗外出游猎的消息。菊儿特勤召集了一大批人,并开始找寻九姓乌古斯汗的行踪。
二人相遇后,干了一仗,菊儿特勤赢得了胜利,吞并了可汗的部队。九姓乌古斯汗逃到了他的城堡。[但是],菊儿特勤用水冲垮了城堡的城墙。然后,菊儿特勤让传令兵向城堡内喊话,宣称会保护投降者并饶恕他们。城堡内的士兵因为饥饿而士气低落,全都从城堡中逃出来请求他所承诺的宽恕。九姓乌古斯汗依然躲在城堡中,菊儿特勤的士兵冲进了城堡并缢杀之。兹后,菊儿特勤就成为了九姓乌古斯的可汗。
(二)九姓乌古斯的特点和惯例
这是他们说的话:九姓乌古斯汗有一千名侍卫和四百名侍女。这一千多人年复一年(或日复一日)每天三餐都和九姓乌古斯汗一起吃,而且想吃多少就有多少。他们每顿饭都能喝到一杯酒,而且这些酒(即产自九姓乌古斯)都是用葡萄酿的。这个汗在平民被驱赶走之前从不外出。并且,当他骑马[脱离队伍]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走在他前面,从他的宫殿沿路跑到城市的边缘;每个地方都或铺或挂着地毯,这个城市的头人当中的一个走在他前面,大声呼喊人们清理出路来。当他从马上下来[进入宫殿],侍卫们把他的马从外院(即外门和内门之间的地方)牵出来,每个人都要跪在他的马前,直到他的马过去。
(三)九姓乌古斯中的摩尼教和其他宗教
九姓乌古斯可汗传统上信仰摩尼教(maδhab-e=Dīnāvarī)。然而,在九姓乌古斯的首都(?ahr)和疆域(welyāyat)内,还有基督教(tarsā)、二神教(θanawī,即拜火教)和佛教(?omanī/ ?amanī,借自粟特语?mn,系梵语?ramana沙门之音转)。九姓乌古斯共有九个大臣(wazīr)。
(四) 九姓乌古斯的法律制裁
在九姓乌古斯人中,如果有人因为盗窃而被捕,那么他就会被戴上脚镣,双手与脖子绑在一起,同时被人用棒子抽打:两百下打在每条大腿上,一百下打在背上。他会被割掉鼻子、割掉耳朵、砍掉双手,然后游街示众,传令者大声喊道:“大家都看看他,不要做他做过的事!”如果一个人与未婚少女私通,那么他会被罚三百鞭子并被罚上交一匹母马和一件由五十锭银制成的长袍。如果是与已婚的女人私通,那就是通奸。两个人都要被带到汗的宫殿,汗会命令抽打每人三百下,而男人必须给那个女人的丈夫一顶由全新的毛毡做顶子的帐篷。然后那个通奸的女人须嫁给那个奸夫,女人原来的丈夫会迫令奸夫再为他找一个女人来,而且奸夫还得付出这个女人的嫁妆。想要做到这些,这个奸夫必须是一个富人,若是穷人,那么他仅仅是被鞭打三百下就可以释放了。如果杀人,那么会被罚以重金,会变得穷困潦倒,然后再被关在监狱里一个月,就可以释放了。同样的,这还是在他是一个富人的前提下进行的。若是一个穷人,那么法官们会把他们关起来并用棒子打,然后放之。
(五)九姓乌古斯的其他特征
九姓乌古斯汗住在一个由栅栏或墙垣围起来的宫殿里。地板上覆以毛毡,毛毡上面铺盖地毯,这些地毯都是由[伊朗和河中地区]的穆斯林用来自于中国的锦缎织成的。然而,九姓乌古斯的普通平民都居住在草原上,住着人字形或框架式帐篷。九姓乌古斯汗的衣服系用中国锦缎或丝绸制成,而普通平民的衣服是由丝绸和亚麻布制成的。这是一种宽大的服式,宽袖长裾,包住全身。九姓乌古斯汗的腰带是用珍珠[和宝石]织成的,而当有大批人来觐见他的时候,他就会戴上王冠。当他骑马外出时,有三万骑士跃马随从。所有人都穿着胸护和铠甲,他们用长矛与敌作战。
(六)通往九姓乌古斯国之路
关于进入这个国家的道路,需先由巴尔浑到达巴尔楚克(Bar?ūk),[26]再从巴尔楚克到龟兹(Ku?a),再从龟兹到焉耆(Ankī),再从焉耆到西州(Sī-kat),再从西州到M. k. ?mignāθūr,再从M. k. ?mignāθūr到中国城,需要一天的行程。[27]
(七) 中国城:那里的摩尼僧
其地比龟兹要小。由二十二个村庄和一处平原组成,冬天很冷,有雪但不大。夏季炎热。当地居民都修地窖,大部分人住在这些地窖里,到夏末才从那些地方转回家里。居民们都扎着腰带,上面挂着刀子、匕首和日常必需品,在当地统治者宫殿的大门附近每天都聚集着三四百个电那勿(Dīnāvarīyān),大声念诵摩尼的著述,然后走向统治者,向他致敬后返回。从中国城(即西州)再向ZYKRD走,就到达九姓乌古斯之地了。
[0]译者注:巴匝尼亚人(Phazania),即今利比亚西南部的费赞(Fezzan)地区。
[①]译者注:高格(Gog)与玛高格(Magog)部落,大致处于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
[②]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Hududal-‘?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Geography 372 A H. - 982 A.D.,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by V. Minorsky, with the Preface by V. V. Barthold)》,伦敦,1937年,第97~98及286页以下。
[③]见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287~289、310页。又参见克泽莱蒂(K. Czeglédy)《迦尔迪齐论中亚史(Gardīzī on the History ofCentral Asia. 745-780 A. D.)》,《东方学报(AOH)》第27卷,1973年,第257页以下页。
[④]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99-100页及304页以下。
[⑤]迦尔迪齐也注意到这个封号,见克泽莱蒂《迦尔迪齐论中亚史》,第259页。但他误解了这个故事。
[⑥]译者注:Deh-e Nō,原文译作New Village,即新村,但同时注明相当于Navē-kaθ。该名又见于《世界境域志》写作Navijkath,米诺尔斯基释为Qocho,即高昌。见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Hudud al-‘?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a Persian Geography 372 A H. - 982 A.D., 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by V. Minorsky, with thePreface by V. V. Barthold)》,伦敦,1937年,第86、234页。应为粟特语,意为新城,当指罗布泊地区的康居聚落。敦煌写本S. 367《沙州伊州地志》记载此地有康居聚落:“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卌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支城”。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5页。故本文径改为“新城”。
[⑦]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277页。
[⑧]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95-96及277页以下。
[⑨]译者注:Bodisatv-Pavard,应为梵语Bodhisattvā-pravridha之音转,意为善辩菩萨。
[⑩]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96-97及282页以下。
[?]译者注:Yigän为突厥语,意为“侄儿或孙子”,常用作男人的名字。这里的Yigän,似乎有贵胄之意。
[?]译者注:?īnānj-kaθ,应即高昌。《世界境域志》写作chinanjkath,米诺尔斯基释为Qocho,即高昌。见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94、195、229、271页。又见佚名著,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9页注2。
[?]译者注:Xusan,又作Küsan,相当于《世界境域志》之Kusan,米诺尔斯基释为龟兹地区。见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232页。
[?]译者注: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4载:“[黠戛斯先人]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牸牛交于此窟。”古代突厥卢尼文碑铭页多次提到黠戛斯境内去曲漫山,如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0、101、125、159页。
[?]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282Y页以下;米诺尔斯基《马尔瓦则论中国与突厥(Sharaf al-Zamān TahirMarvazi on China,the TurksandIindia.)》,伦敦,1942年,第30、161~162页。
[?]写本中的这个词不清楚,或许为F?YNWN,抑或为V?YNWN。该术语可能有两个单词构成,第一个是突厥语之bügü、büyi等,意为“符咒”“咒语”“魔法”“法术”,拉德洛夫(W. Radloff)《突厥语方言词典试编(Versuch eines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 mit einem Vorwort von Omeljan Pritsak)》第4卷,海牙,1960年,第1874、1883页。纳蒂尔亚耶夫(Nadyelyayev)认为该词之缩略形式为bügü,意为“智者”、“圣人”。科瓦列夫斯基(Kowalewski)认为是蒙古语böge/büge,意为“萨满”“术士”。第二个词似乎与蒙古语俗语之“符咒”“治病魔法”“痊愈”有关,见莱星(F. D. Lessing)编《蒙英词典(Mongolian-EnglishDictionary)》,伯克利,1975年,页260b。参见米诺尔斯基《马尔瓦则论中国与突厥》,第30、124页。
[?]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92页以下及254页以下。
[?]译者注:Al?ān,观其读音,或为阿拉善。然观其地望,似又不妥。存疑。
[?]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98页及292页以下。
[?]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289~290页。
[21]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292页。
[22]参见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273~274、296页。
[23]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9~95页及263页以下。
[24]译者注:Dīnāvarī,为“真正信仰”之意,亦即敦煌写本BD00256《波斯教残经》所见的“电那勿”的对应词。据考,应指摩尼教的专职修道者。见芮传明《帕提亚语“摩尼致末冒信”的译释与研究》,《史林》2010年第4期,第78页注3。参见格施威彻(I.Gershevitch)《摩尼教粟特语语法(A Grammar of Manichaean Sogdian)》,伦敦,1961年,§1943。
[25]Agni,即今焉耆。见沙畹(EdourdChavannes)《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圣彼得堡,1903年,第113页;斯坦因(A. Stein)《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AsianTracks)》,伦敦,1933年,第276页以下。
[26]Bar?ūk,又见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293~294页。
[27]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273页。其中的Sī-kat,即西州,见布莱希乃德(E. Bretschneider)《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Fragments towardthe Knowledg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from the13th to 17th Century)》第2卷,伦敦,1889年,第243页。
[28]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83页以下、第223页以下。
[29]译者注:Bag-?ūrā,在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中写作Bughshūr,言其“是中国一个大城。城中住着许多来自个承德商人,这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地方。”(第229页)王治来考证说:“这是一个伊朗语的地名,其意义为‘盐水形成的沼泽’,密诺尔斯基认为是指四川重庆附近的自流井,是一个制盐工业的中心。这说明粟特人经商,到了长江流域。”见佚名著,王治来译注《世界境域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1页注3。
[30]译者注:Sanglāx,马尔丁奈兹(A. P. Martinez)认为无疑是哈密以东的石城(Ta?-Balig)。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有载,作Sanglākh:“为沙州地区一大村。居民为偶像崇拜者。”(第229页)由是以观,其地应在沙州。再从下文所载,由Sanglāx到肃州(今甘肃酒泉)
[31]译者注:Sax-?au,失考。视其音,观其地望,应为肃州(今甘肃酒泉)。从文献记载看,由Sanglāx到肃州为七日行程,而由肃州至甘州为三日行程,是知Sanglāx应在沙州城与哈密城之间。
[32]译者注:Ku?a,观其读音,应为龟兹,但显然是不可能的。待考。
[33]参见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冯家昇(Feng Chia-sheng)《中国社会史——辽(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费城,1949年,第264、301页。
[34]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299页以下及260页。
[35]译者注:P’Y?,其地不详,或为新疆拜城。
[36]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85~86页、234页。
[37]译者注:toronj,马尔丁奈兹译作Oranges,应为桔子、橙子,但桔子、橙子应为南方产品,不闻历史上和田一带有此类物产。存疑。
[38]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289页以下。
[39]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267页以下、271-272页。
[40]Kü?eng-Qan,即高昌回鹘亦都护,都于北庭,传统汉文史料称其为高昌回鹘辖下之地。布莱希乃德《中世纪研究》第1卷,第244页以下;第2卷,第27页以下。
[41]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291页。
[42]米诺尔斯基整理《世界境域志》,第298、34页。参见哈密顿(J. R. Hamilton)《五代回鹘史料(Les Ouï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ès les documents chinois)》,巴黎,1955年,第1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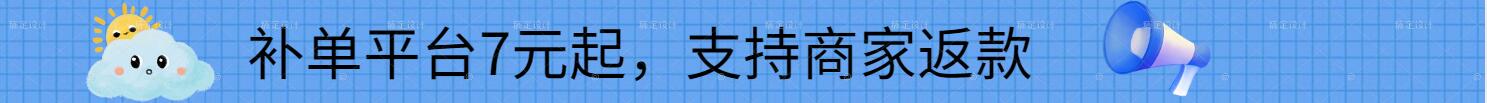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